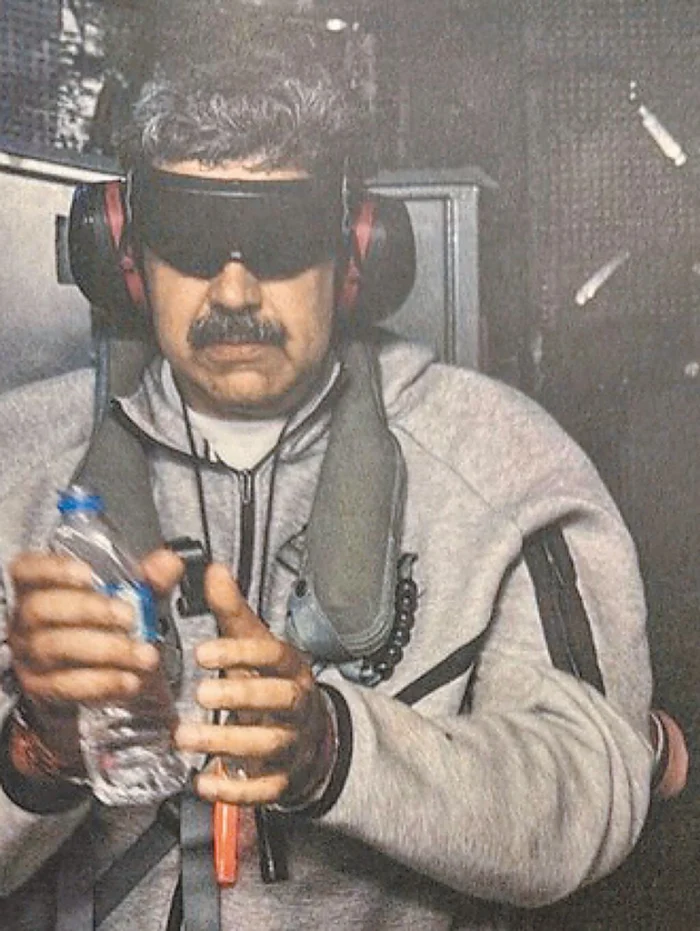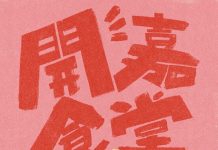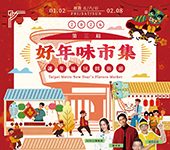文/邱榮舉
(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前副院長、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專案代表)
針對長庚大學湯明哲校長主張「辦醫學院既貴又辛苦,教育部應壯士斷腕」(聯合新聞網2025年8月23日報導),筆者認為此論點過於狹隘,將大學教育簡化為企業式的成本計算,忽略了醫學教育背後所承載的國家戰略、社會責任與長期人才培育使命。
《大學法》第1條明確指出:「大學以研究學術,培育人才,提升文化,服務社會,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。」不論是醫學院或其他學院,都應以此為最高原則。如果教育只是追求「便宜、省力」,那麼開補習班或職訓中心或許更符合邏輯。然而,高等教育從來不是廉價產業,而是國家對知識、文化與人才的長遠投資。醫學教育特別昂貴,正因為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不可妥協。若僅因「既貴又辛苦」便主張「熄燈止損」,形同放棄醫療人才培育與公共衛生的國家責任。
湯校長以「不符最小經濟規模」為理由,批評清華、中興、中山三校學士後醫學系一年僅招收23人,不符美國四年制醫學系每年至少100人的規模。然而,若依此邏輯,偏鄉教育、偏鄉醫療乃至偏鄉交通都因規模不足而不符成本效益,是否也應廢止?公共服務正因市場無法自我維繫,才需要國家介入。醫學教育的價值更不能僅以帳面數字計算,其意義遠超過「最小經濟規模」所能涵蓋。
事實上,臺灣近年設立的學士後醫學系公費制度,已有一定成效,並肩負著解決偏鄉醫療不足、長照需求、戰地醫護及基層社區醫師培訓等國家戰略性任務。當前兩岸關係緊張,醫療人才更是國防與社會安全的重要支柱。這些布局本該持續支持,而非因單純成本思維而突然喊停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更應密切合作,整體規劃、質量並重,以長遠戰略視野推動醫學教育,而不是用「止損」的短線思維斷送未來。
值得回顧的是,長庚紀念醫院於1976年由王永慶為紀念其父王長庚而創辦,當時並非立即具備完善體系。長庚醫學院自1987年起步時,也只是招收學士後醫學系學生,並非一開始就擁有完整規模。今日的長庚體系能有成就,正是因為願意「萬丈高樓平地起」。這段歷史提醒我們,醫療體系的建構需要耐心與時間,沒有起步,何來茁壯?
更何況,湯校長援引美國制度,卻忽略了其結構性問題:高額學費與醫療費用造成普遍經濟壓力,並未真正解決社會需求。若我們盲目模仿「其形」,卻不思考「其本」,最終只會重蹈覆轍。
醫學教育的評估固然需要兼顧效率與品質,但「效率」不能取代「公平」,「成本」不能凌駕「使命」。在高齡化、偏鄉醫療不足及國防醫療需求的背景下,臺灣更需要的是長遠戰略與社會使命的堅持,而不是用「最小經濟規模」來簡化複雜的國家責任。若以企業盈虧邏輯來決定醫學教育的存廢,最終受害的將是最需要醫療資源的人民。
(本文經洞傳媒授權轉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