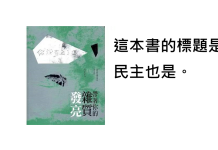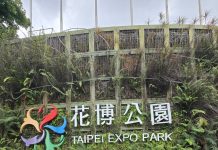「114年節約能源表揚大會」樹立節能典範
墨新聞|新聞策劃編輯部記者李婉如/綜合報導
為表揚節能績效卓著企業與推動能源教育績優學校,經濟部於今(15)日下午3時30分在台北遠東香格里拉飯店舉辦「114年節約能源表揚大會」,由部長龔明鑫與教育部次長朱俊彰出席頒獎,今年節能標竿單位包括24家公、民營機構及12所國民中小學,為我國能源轉型樹立節能典範。
經濟部表示,面對全球淨零轉型挑戰,臺灣正全力推動二次能源轉型。「深度節能推動計畫」自113年啟動以來,政府持續引領企業落實深度節能,協助產業升級轉型,打造能源與經濟雙贏的新局面。截至今(114)年12月,累計節電已達104億度,相當於250萬戶家庭年用電,成果亮眼,今年的得獎單位也象徵產業界在深度節能上的突破。
經濟部能源署進一步說明,節能標竿獎透過示範效應帶動各產業自主投入節能。今年獲獎單位更由數位化邁向 AI 智慧化與系統化改善,將能源管理從「人工經驗」提升至「科學數據」的精準掌控,展現智慧科技與跨領域整合的創新能力。本屆節能標竿得獎單位共節電1.9億度,相當於4.7萬戶家庭一年用電量,併同節省天然氣、蒸氣等其它能源,合計節約9.3億元能源成本,減少約13.9萬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,等同360座大安森林公園1年的碳吸附量,再創深度節能的亮眼佳績。
本屆獲獎的 6 家金獎,各自展現鮮明的節能亮點與特色。中鋼公司軋鋼一廠結合集團資源與內部研發量能,跨部門合作找出產線能源使用的關鍵因素,並導入AI 演算法預測與控制,有效降低能源耗用。同時,中鋼亦建立完善節能提案與獎勵機制,鼓勵同仁積極參與,進一步擴大整體節能成效;漢翔航空發動機事業處建置水、電、氣一體化的能源管理監控系統,即時警示與掌握設備運轉狀況,精準量測與節能效益驗證,實現高度專業且細緻的智慧製造管理。
華邦電子高雄廠自建廠初期即全面導入節電設計,推動數位治理並建立五大數位平台,整合能源、設備與生產資料,提升能源使用效率,並推動全員自主參與節能行動與提案,形塑企業內部節能文化;鼎霖國際以智慧倉儲管理優化製程動線與加工排程,減少待機時間與人為錯誤,並導入能源監控系統及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,讓企業從「憑感覺節電」轉型為「以數據掌握用電」。
高雄長庚醫院展現全院一致的節能決心,自高層提出提升空調末端風量的構想後,團隊歷時近半年測試,最終改採直流馬達風扇以增加風量、減少過度降溫,讓用電量下降約二至三成;臺北醫學大學推動「綠色實驗室」計畫,擴大節能措施至各實驗室場域,並整併空調冰水系統,導入智慧水泵控制與高效主機汰換,全面提升空調效能,此外,也將永續教育納入教職員必修學分,以多元作法推動節能與永續發展。
在能源教育方面,4所學校榮獲金獎,透過課程創新、軟硬體設施建置及社區推廣,深化學生能源素養。例如:宜蘭縣員山國中將永續發展目標(SDGs)搭配能源議題,融入自然、社會及國語文等跨領域學科;高雄市大樹國小規劃能源教育廊道及永續能源體驗專區,搭配「問題導向(Problem-Based Learning,PBL)教學策略」及互動式能源展示空間,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環境責任思辨能力;臺中市永安國小建置「創能、儲能及節能概念」綠能手作教室,串聯臺中海區策略聯盟學校,擴大能源教育影響力;臺北市興雅國小發展探究式學校本位課程,並培育「能源小尖兵」返家調查用電情形,將節能理念延伸推展至家庭及社區。
能源署最後說明,為擴散節能標竿獲獎單位之經驗分享及技術傳承,預計明(115)年辦理標竿選拔與示範交流觀摩會,屆時歡迎各界踴躍報名。另為協助各界快速查找歷年標竿節能措施案例,雲端資料庫提供關鍵字搜尋及案例推薦功能,以加速節能技術與典範經驗推廣。
相關資訊可至「節約能源園區(EnergyPark)」網站
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: 「114年節約能源表揚大會」樹立節能典範
香氣「菇」鼻 南澳段木香菇評鑑品味山林醞釀的醇厚
墨新聞|記者農夫林/宜蘭報導
林業署宜蘭分署與宜蘭縣南澳鄉公所15日於南澳段木香菇巴萊體驗館舉辦「2025年宜蘭縣南澳鄉段木香菇巴萊(Papak Khoni Balay)評鑑競賽」由南澳眾多職人菇農角逐冠軍,並藉由競賽過程中,認識南澳香菇產業、南澳特色及泰雅原民文化等,並一同窺探冠軍菇農王鴻文的得獎香菇,此活動除延續每年香菇評鑑及原民文化外,更創造在地觀光、推展林下經濟及國產材多元應用。
活動延續每年評鑑精神理念,以認證國產材為獎盃外,將6大指標逐一評測以選出每年最高品質香菇,並由宜蘭縣政府、宜蘭分署、南澳鄉民代表會、農業試驗所、磐石生活科技有限公司宜蘭分公司、南澳各村辦公室、南澳鄉香菇產銷班第1班、在地菇農及現場民眾共同參與,透過評鑑過程與體驗館,介紹當地農特產品及原民文化特色產品;另評鑑賽藉由專業委員對香菇身家進行各項評鑑,包含「直徑大小與開度」、「重量」、「外觀」、「菇體彈性」、「香氣」等項目評分,各菇農精挑最完美香菇競賽。
透過專家評鑑結果出爐,冠軍由王鴻文拿下、亞軍由蔡淑真拿下、季軍由鄭瀚彥拿下、優等由鐘文明、張黃玉琴、范守臣拿下。
宜蘭分署表示,每年的段木香菇巴萊評鑑賽相當精采,集結各輔導陪伴單位、在地菇農及原民社區,增加地方凝聚力,一同創生地方產業及林下經濟,透過每年度評鑑競賽,打造南澳段木香菇品牌及國產材多元利用,希望民眾藉由競賽過程提高香菇品質,認識段木香菇的產銷過程,購買南澳鄉高品質產品。
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: 香氣「菇」鼻 南澳段木香菇評鑑品味山林醞釀的醇厚
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: 香氣「菇」鼻 南澳段木香菇評鑑品味山林醞釀的醇厚
冷吱吱!太平山及燈篙林道仍吸引不少遊客踏青
墨新聞|記者農夫林/宜蘭報導
今年入冬以來首波大陸冷氣團於14日晚間起影響全台,海拔約2.000公尺的太平山遊樂區出現濃霧,溫度僅有3度,體感溫度更低,與平地溫差明顯,仍有許多遊客不畏寒冷前往賞景。此外,宜蘭員山的燈篙林道也成為遊客新寵,這條步道兩旁種植各種櫻花,每年2至3月都會綻放成櫻花林,雖然目前尚未到花期,但已有遊客前往踏青。
太平山遊樂區內宜專一線8.5K處近期上邊坡持續發生坍方,先前僅開放部分園區,15日上午7時30分恢復開園。林業署宜蘭分署表示,這波大陸冷氣團,太平山遊樂區僅出現濃霧,溫度僅有3度,體感溫度更低,但仍有許多遊客不畏寒冷前往賞景。
冷吱吱,員山的燈篙林道發生了違規露營事件。有民眾15日上午前往健行時,發現在山頂處有人搭起一頂綠色帳篷,帳篷外還擺放著鞋子。該民眾嘗試勸導帳篷內的人,但對方沒有回應,只好通知園區志工。等志工抵達現場時,帳篷已經不見蹤影。其他民眾表示,由於當地有公告禁止露營,應該遵守相關規範,做一個守法的公民。
燈篙林道促進會總幹事林建成呼籲遊客不要在該區域露營。他強調,雖然這裡是公有地,促進會沒有強制執法權,但仍希望露營的朋友們能夠配合規定。
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: 冷吱吱! 太平山及燈篙林道仍吸引不少遊客前往
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: 冷吱吱!太平山及燈篙林道仍吸引不少遊客踏青
「桃園市商業轉型服務中心」成果發表
墨新聞|新聞策劃編輯部記者李婉如/綜合報導
桃園市政府積極推動商業服務業升級轉型,為掌握市場趨勢並提升產業競爭力,特成立「桃園市商業轉型服務中心」,從數位力、永續力、品牌力三大核心面向協助本巿業者加速轉型。今(15)日舉行的成果發表會中,不僅表揚10家在今年展現卓越轉型成效的標竿企業,體現桃園商業蓬勃的創新能量,也同步向市民介紹4家新進駐桃園舊城區的特色店家,展現桃園城市更新與商業活力的雙重成果。
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表示,今年度商業轉型服務中心延續「推數位、助永續、創品牌」三大核心策略,針對本市餐飲、批發零售及各類服務業者,提供專業顧問諮詢、客製化輔導,並協助申請各項政府資源,形成完整的轉型陪伴鏈。中心團隊全年深入走訪109家業者,協助店家成功取得近860萬元政府補助與資源,同時精選10家具潛力業者進行客製化輔導,打造桃園商業轉型的標竿示範。在專業輔導與精準策略的帶動下,這10家標竿企業共創造逾4,500萬元產值與營收成長,充分展現桃園在推動商業升級、促進產業創新上的具體成果與強大動能。
在「品牌力」強化上,透過體驗優化與市場拓展提升品牌競爭力。「鹿馬岸南島人文主題餐廳」共同創辦人趙哲櫻表示,透過本次升級轉型,餐廳導入顧客分級服務、行動點餐與標準化流程,有效提升營運效率並降低掉單率;同時強化人才培訓與品牌永續定位,推出多語菜單與「南島盛宴」產品,使營收成長5%、客單價提升10%,未來將持續推動文化永續並擴大餐飲據點。「咖THAI」負責人陳威廷分享,品牌以創意泰式料理為核心,本次透過計畫完成品牌識別重塑、空間動線與軟裝優化、多語菜單更新,並導入線上點餐與訂位系統。改造後開幕首週即帶動營收成長23%,來客數與網路聲量同步提升,朝成為桃園代表性泰式餐飲目標持續邁進。
在「數位力」推動上,成功協助業者導入智慧科技提升效率。例如「太創數位股份有限公司」導入「訂食堂」商辦訂餐平台,整合APP 線上訂餐、LINE Pay支付、機器人自動結單系統,並全面採用無一次性餐具與電子發票。透過數位管理,不僅創造450萬元新增產值、新增10個就業機會,更減少1.27公噸 CO₂e排放。在「永續力」方面,配合淨零趨勢,引導業者將永續納入商業模式。百年老店「大房食品有限公司」推出環保與低碳包裝,並將製程副產物(豆渣)轉化為高附加價值產品,成功落實循環經濟並降低環境負擔。
桃園市政府自去(113)年起推動舊城再生計畫,已完成部分老舊建築外牆優化,並重新規劃街道設計與人行空間,硬體改善已初見成效;今年度經發局以「特色店家進駐桃園舊城區補助及輔導計畫」,成功輔導十三個手感烘焙坊、神明神明雞蛋糕、沐雪冰城及炭秀等4家青年創業及原民等特色店家進駐,目標為活化舊城區,打造成為具文化深度的老城新生商圈,透過此計畫,不僅成功活化老舊空間、創造就業機會,更透過品牌與文化的雙軸升級,全面提升桃園舊城區的商業競爭力。
為協助商業服務業建立減碳經營、智慧管理、數位轉型與生成式 AI 等新思維,進一步提升業者的轉型意願與永續軟實力,今年度共辦理6場專業課程,實體及線上共培訓18,331人次。透過系統化學習,成功引導業者跨足多元知識領域,掌握市場趨勢與數位工具,持續激發創新能量。
對店家與商圈而言,持續創新經營模式,是在競爭市場中站穩腳步、持續成長的關鍵。桃園市政府透過「商業轉型服務中心」,為商業服務業打造更友善的升級環境, 今年轉型成果亮眼,不僅為地方帶來實質的經濟效益,也成功打造多個具示範性案例。未來,在市府的持續支持下,將能更自信地迎接市場變化、拓展客群,共同形塑桃園成為更具魅力與前瞻性的嶄新城市。(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廣告)
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: 「桃園市商業轉型服務中心」成果發表
稅捐機關唯一獲獎 中市地稅局再奪行政院第8屆政府服務獎
墨新聞|記者馬源培/台中報導國家發展委員會今(15)日在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國際會議廳辦理第8屆「政府服務獎」頒獎典禮,由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親自頒獎表揚。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繼108年榮獲第2屆政府服務獎後,再次以智慧創新服務成果脫穎而出,憑藉「地方稅AI客服任意門—打通一站式稅務服務雲」方案,從144個參賽機關中脫穎而出,榮獲「第8屆政府服務獎—數位創新加值」獎項,充分展現落實市長盧秀燕推動智慧城市與數位治理的施政成果。
地稅局長沈政安表示,地稅局於107年全國首創AI智慧客服,並於111年獲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補助經費,及授權規劃建置全國版地方稅AI智慧客服「地稅小幫手」。該系統除提供完整的地方稅務即時問答外,更持續加值串接稅額試算、線上申辦及電子繳稅等功能,有效協助民眾解決不熟悉稅法、不清楚稅額、申辦流程與繳稅方式等問題,成功打造貼近民眾需求的一站式全方位智慧稅務服務。
沈局長進一步指出,「地方稅AI客服任意門」系統的服務覆蓋率與回答精準度均超過9成,並提供24小時、全年無休的服務模式。系統自上線以來,使用人次已突破16萬,其中有5成是在非上班時間,顯示這項智慧服務有效解決上班族請假洽公的問題,且有超過9成使用者給予5星的高滿意評價。
沈局長強調,「政府服務獎」素有行政機關奧斯卡金像獎之稱,競爭激烈、獲獎不易,在盧市長積極推動數位治理與智慧城市的政策引領下,「地方稅AI客服任意門」充分展現智慧科技導入公共服務的具體成效。此次榮獲政府服務獎的最高肯定,正是台中市數位治理成果的最佳見證。未來地稅局將持續精進系統功能,提供民眾更即時、便利且友善的數位稅務服務。
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: 稅捐機關唯一獲獎 中市地稅局再奪行政院第8屆政府服務獎
殯葬管理表現亮眼! 台中獲中央「優等」肯定 今表揚業者感謝齊力提升殯葬服務
墨新聞|記者馬源培/台中報導為提升殯葬服務品質並保障消費者權益,台中市政府每年分三大區域輪流辦理合法殯葬業者評鑑。今年針對第三區域(北區、中區、西區)120家禮儀服務業及9家私立殯葬設施進行評鑑,選出11家特優、2家優等及8家甲等業者,今(15)日在林皇宮舉行表揚典禮暨殯葬業務講習會。民政局副局長彭岑凱代表市長盧秀燕出席頒發獎牌,肯定業者投入生命事業的努力與創新,並期許持續精進服務,與市府攜手提供家屬更周全的協助。
彭副局長表示,在市府團隊與殯葬業界通力合作下,台中市於內政部「114年度殯葬管理業務績效評量」中榮獲「優等」,較112年「甲等」大幅躍進。此項佳績歸功於業界的積極配合與市府同仁的努力,展現市府推動「溫暖施政」的具體成果,也期盼公、私部門持續協力配合,發揮相得益彰的效果,提升各項殯葬服務品質及量能,提供市民更優質、便捷的殯葬服務。
彭副局長指出,市府持續推動殯葬革新建設,今年陸續啟用太平、大肚及沙鹿樹葬區,全市樹葬區增至8處;另太平與東勢生命紀念館預計明年3月啟用,北屯生命紀念館則規劃於116年完工;而崇德殯儀館原地改建、大甲殯儀館新建20間靈堂,以及各區納骨塔修繕與增設櫃位,也正穩健推進,期盼為家屬打造更舒適、更有尊嚴的治喪環境。
生管處長柯宏黛提到,今年評鑑中可見多數業者積極接軌國際ESG(環境、社會、治理)發展趨勢,不僅在喪葬儀節中落實性別平權理念,如女兒捧斗、女性封釘等作法,也推動以米代金等環保節葬措施,並結合科技創新服務,展現兼顧人文關懷與永續發展的專業精神。此次特殊榮譽獎項中,共有10家業者獲頒性別平等獎、16家環保永續獎、5家創新服務獎及3家人文關懷獎,充分展現殯葬業多元且具前瞻性的發展成果。
生管處表示,除表揚優良殯葬業者外,今年講習會也著重提升業者專業知能,緊扣時代趨勢,特別邀請「冬瓜行旅」郭憲鴻先生主講「科技浪潮下的『人』:我們在AI時代的角色與航程」,深入探討在 AI 時代背景下,業者如何回歸本質,強化並展現「以人為本」的服務價值。
生管處補充,今年共120家禮儀服務業及9家私立殯葬設施參與評鑑,經評鑑小組綜合評選結果有11家榮獲特優,分別為宇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佑宇興業有限公司、幸福生命企業有限公司、致知興業有限公司、弘一生命事業有限公司、青山禮儀有限公司、祥和生命事業有限公司、祥華禮儀有限公司、華梵禮儀有限公司、楊子佛教禮儀股份有限公司、蓮池禮儀股份有限公司;另福元儀典生命禮儀有限公司及德華齋有限公司則獲優等。
此外,甲等業者包括金陵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大明生命禮儀有限公司、吉品生命事業有限公司、欣欣禮儀有限公司、冠昇生命事業有限公司、翊嘉禮儀有限公司、普安禮儀有限公司及勝隆禮儀社等。相關評鑑成果並已公布於生管處官網「評鑑優良名單」專區( https://reurl.cc/33X2dR ),提供民眾查閱參考。
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: 殯葬管理表現亮眼! 台中獲中央「優等」肯定 今表揚業者感謝齊力提升殯葬服務